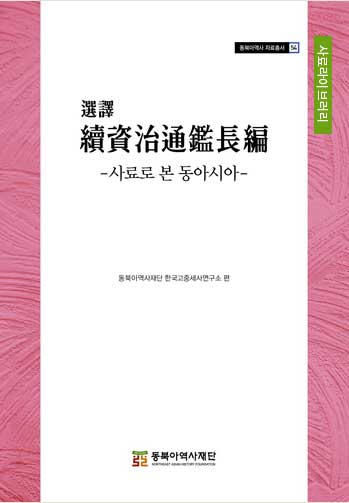요(遼)의 국신사(國信使)를 작별하는 잔치에서 요의 군주에게 답하는 참지정사(參知政事)의 글
丙寅, 遼國信使蕭禧等辭于紫宸殿, 置酒垂拱殿. 答遼主書曰, “兩朝繼好, 六紀于茲, 事率故常, 誼存悠久. 比承使指, 諭及邊陲, 已約官司, 偕從辨正. 當守封圻之舊, 以需事實之分, 而信介未通, 師屯先集, 侵焚堠戍, 傷射巡兵. 舉示力爭, 殊非和議. 至欲當中獨坐, 位特改于臣工. 設次橫都, 席又難于賓主. 數從理屈, 纔就晤言. 且地接三州, 勢非一概, 輒舉西陘之偏說, 要該諸寨之提封. 屢索文憑, 既無據驗. 欲同案視, 又不準從. 職用乖違, 滋成濡滯. 竊慮有司之失指, 曾非與國之本謀. 茲枉軺車, 再垂函問, 重加聘幣, 彌見歡悰. 然論疆事之侵, 盡置公移之顯證. 述邊臣之議, 獨尤病告之愆期. 深認事端, 多非聞達. 重念合天地鬼神之聽, 共立誓言. 守祖宗疆土之傳, 各完生聚. 不嗇金繒之巨萬, 肯貪壤地之尺尋? 特欲辨論, 使無侵越, 而行人留館, 必於分水以要求. 樞府授辭, 期以興師而移拆, 豈其歷年之信約, 遂以細故而變渝. 已案輿圖, 遙爲申畫, 仍令職守, 就改溝封. 遐冀英聰, 洞加照悉.” 參知政事呂惠卿之辭也.
初, 蕭素·梁穎既與劉忱·呂大忠會議地界, 久不能決, 故遣禧復來, 命韓縝·王師約館伴. 禧既致國書, 又出其國劄子一通以進, 其大指如素·穎所言, 且以忱等遷延爲言. 縝等日與禧論難, 禧但執以分水嶺爲界, 然亦不別白何處爲分水嶺也. 詔諭以兩朝和好年深, 今既欲委邊臣各加審視, 尙慮忱等所奏未得周悉, 已改差縝同張誠一乘驛詣境上, 和會商量. 令禧以此歸報, 禧不受命. 又遣內侍李憲齎詔示之, 許以長連城·六蕃嶺爲界, 而徙並邊遠探鋪舍于近裏. 長連城·六蕃嶺, 治平二年契丹嘗於此置鋪矣, 邊人以其見侵毀之, 後不復來, 至是許其即舊址置鋪, 而禧猶不從, 執議如初.
上不得已, 議先遣沈括報聘, 于是樞密院言, “本朝邊臣見用照證長連城·六蕃嶺爲界, 公牒六十道, 多是北界聲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或交蹤, 並在長連城·六蕃嶺之北, 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八日牒稱, 南界送到於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捉賊人張奉遠等, 不合過界, 準法斷訖. 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牒, 捉到截奪南界代州
崞縣
赤埿膠主戶白友牛賊人事, 既指長連城分水嶺上爲兩界, 并稱白友係代州崞縣主戶, 顯見不以古長城并近裏分水嶺爲界. 治平二年起移北界鋪舍, 即無侵越地界. 今聖旨只爲兩朝通和歲久, 所以令於長連城·六蕃嶺南依舊址修蓋, 已是曲敦和好. 今禧更指分水嶺爲界, 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 皆謂之分水嶺. 昨蕭素等所執照證文字三道, 除大石·義興冶兩寨已爲北界侵越, 不經治平年發遣, 見不以長連城爲界外, 其西陘寨執張慶文字爲據, 言分水嶺上有土隴, 據所指處即無土隴. 兼張慶文字指雁門寨地至北界遮虜軍十一里, 今雁門寨至長連城約八九里, 長連城至遮虜軍約二里, 又證得長連城爲界. 兼忱等曾牒素等, 令指定是何山名爲分水, 素等牒回, 但稱‘沿邊山名·地里·界至, 南界足可自知, 豈可移文會問?’ 顯見原無指定去處. 今禧所執, 與素等同, 全無照驗文字. 欲令沈括等到北朝日, 將見用照證文字, 一一聞達北朝.”
詔, “國家與契丹通和年深, 終不欲以疆埸細故有傷歡好大體. 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址修蓋, 務從和會, 即更不論有無照證, 若不指定分水處, 即恐檢視之時, 難爲擗撥. 一, 李福蠻地, 許以見開壕塹處分水嶺爲界. 一, 水峪內義兒馬鋪并三小鋪, 即挪移近南, 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爲界. 一, 自西陘寨地方, 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探·白草鋪山頭分水嶺向西接古長城爲界. 一, 黃嵬山地, 已經仁宗朝差官與北界官吏於聶再友等已侵耕地外, 標立四至訖. 及天池廟, 順義軍牒稱地理係屬寧化軍, 並無可商議. 一, 瓦窰塢地, 前來兩界官司商量未了, 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 擗撥處以分水嶺爲界.”
上遣使者持報書示禧, 禧乃辭去, 括候禧去乃行. 故事使者留京不過十日, 禧至以三月庚子, 既入辭, 猶不行, 與縝等爭論或至夜分, 留京師幾一月. 蕭禧之再來, 上遣入內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裴昱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 曰, “朝廷通好北朝幾八十年, 近歲以來, 生事彌甚. 代北之地, 素有定封, 而輒造釁端, 妄來理辨. 比敕官吏, 同加案行, 雖圖籍甚明, 而詭辭不服, 今橫使復至, 意在必得. 朕以祖宗盟好之重, 固將優容, 敵情無厭, 勢恐未已, 萬一不測, 何以待之. 古之大政, 必詢故老, 卿夙懷忠義, 歷相三朝, 雖爾身在外, 乃心罔不在王室, 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 密具以聞, 朕將親覽.”
琦言, 臣晚年多病, 心力耗殫, 日欲再乞殘骸, 保此頹暮. 不意陛下以北敵生事, 深思預防, 記及孤愚, 曲有詢逮, 敢不勉竭衰殘, 少塞聖問. 臣竊以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 蓋一百七十餘年矣. 自石晉割地, 并有漢疆, 外兼諸戎, 益自驕大, 在祖宗朝屢常南牧, 極肆凶暴. 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彼角哉? 終愛惜生靈, 屈就和好, 凡疆埸有所興作, 深以張皇引惹爲誡. 以是七十年間, 二邊之民各安生業, 至于老死, 不知兵革戰鬬之事, 至仁大惠不可加也. 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 敵人素以久強之勢, 于我未嘗少下, 一旦見形生疑, 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 雖聞彼主孱而佞佛, 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 造此釁端? 故屢遣橫使, 以爭理地界爲名, 觀我應之之實如何耳. 所以致彼之疑者, 臣試陳其大略.
高麗臣屬契丹, 于朝廷久絕朝貢, 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 且高麗小邦, 豈能當契丹之盛? 來與不來, 國家無所損益, 而契丹知之, 謂朝廷將以圖我, 此契丹之疑也. 秦州古渭之西, 吐蕃部族散居山野, 不相君長, 耕牧自足, 未嘗爲邊鄙之患. 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 殺其老小以數萬計, 所費不貲. 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 即契丹壻也, 既恐闢地未已, 豈不往訴? 而契丹聞之, 當謂行將及我, 此又契丹之疑也.
北邊地近西山, 勢漸高仰, 不可爲塘泊之處, 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 冀其成長, 以制敵騎. 然興於界首, 無不知者, 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 鄣塞要路’, 無以異矣. 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 但使契丹之疑也. 河朔義勇·民兵, 置之歲久, 耳目已熟, 將校甚整, 敎習亦精, 而忽然團保甲, 一道紛然. 義勇舊人, 十去其七, 或撥入保甲, 或放而歸農, 得增數之虛名, 破可用之成法, 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自彼來辨理地界, 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 一例差官檢討, 修築城壘·開淘壕塹, 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 敵樓·戰棚之類, 悉加完葺增置, 防城之具, 率令備足, 逐處兵甲器械, 累次差官檢視, 排朶張盤, 前後非一. 又諸處創都作院, 頒降新樣, 廣謀造作, 澶州等處創爲戰車. 此皆衆目所覩, 諜者易窺, 且敵人未有動作, 彼無秋毫之損, 而我已費財殫力, 先自困弊, 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
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 各專軍政, 州縣不得關預. 雄州地控極邊, 亦設將屯, 其隨軍衣物, 有令兵士已辦者, 有令本營增置者, 有令官造給付者, 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 準備隨行, 明作出征次第, 不可蓋掩, 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 夫北朝素爲敵國, 設如此, 則積疑起事, 不得不然, 亦其善自爲謀者也. 今橫使再至, 初示偃蹇, 以探視朝廷. 況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 若優容而與之, 實慮彼情無厭, 浸淫不已, 誠如聖詔所諭, 固不可與. 或因而不許, 彼遂持此以爲已直, 縱未大舉, 勢必漸擾諸邊, 卒隳盟好.
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 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 自顧老朽, 夙夜思之, 其將何策上助聖算. 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 言及而不言謂之隱. 臣昔曾言散青苗錢不便事, 而言者輒肆厚誣, 非陛下之明, 幾及大戮. 自此新法之下, 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 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 今親被詔問, 事繫國家安危, 言及而隱, 是大不忠, 罪不容誅矣. 臣嘗竊計, 始爲陛下謀者, 必曰, ‘自祖宗以來, 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 非變不可也. 治國之本, 當先有富強之術, 聚財積穀, 寓兵於民, 則可以鞭笞四夷, 盡復唐之故疆, 然後制作禮樂, 以文太平.’ 故始散青苗錢, 使民出利, 所得之利, 復以爲本, 但務多取, 歲增本錢, 無有定數.
又有免役之法, 自上等以至下戶, 皆令次第出錢, 募人應役. 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 故其間時有破敗者, 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 安然無事, 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 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 雖百端補救, 終非善法. 又役錢之內, 每歲更納寬賸錢以備他用, 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 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 一年兩次, 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 今納青苗與役錢, 已是加賦, 有過限者, 亦依二稅法科校, 則是一戶一歲之中, 常負六次科校, 民不勝駭矣. 稍遇水旱, 則逋負官錢, 流移失業, 是已著見, 孰敢言者. 又內外置市易務, 盡籠天下商旅之貨, 官自取利, 主以得利爲功, 錐刀必取, 小商細民遂無所措手.
加以新制日下, 更改無常, 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 稍有違者, 坐以徒刑, 雖經赦降, 去官不得原免. 監司督責, 以刻爲明, 簿法之苛, 過於告緡, 故州縣之間, 官吏惴惴然, 日苟一日, 皆以脫罪爲幸. 夫農者, 國之根本也. 商者, 能爲國致財者也. 官吏者, 助朝廷之敎化者也. 今農者則怨於畎畝, 商者則嘆於道路, 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 恐陛下不能盡知也. 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 而先使邦本困搖, 衆心離怨, 振古以來, 未聞能就此功者也. 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 知其所誤, 能改不吝, 聖人之大德也. 又今好進之人, 不顧國家利害, 但謂邊事將作, 富貴可圖.
獻策以干陛下者, 必云, ‘敵勢已衰, 特外示驕慢耳. 以陛下神聖文武, 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敵境, 則幽薊之地, 一舉可復.’ 此又未之思也. 今河朔累歲災傷, 民力大乏. 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 新選將官皆麄勇. 保甲新點, 未經訓練. 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 糧道不給, 敵人四向來援, 腹背受敵, 欲退不可, 其將奈何? 此太宗朝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 猶以致岐溝之敗也.
臣愚, 今爲陛下計, 謂宜遣使報聘, 優致禮幣, 開示大信, 達以至誠,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 乃修備之常, 與北朝通好之久, 自古所無, 豈有他意, 恐爲諜者之誤耳. 且疆土素定, 當如舊界, 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 不可持此造端, 欲隳祖宗累世之好, 永敦信約, 兩絕嫌疑. 望陛下將契丹所疑之事, 如將官之類, 因而罷去, 以釋彼疑.
萬一聽服, 則可遷延歲月, 陛下益養民愛力, 選賢任能, 疏遠姦諛, 進用忠鯁, 使天下悅服, 邊備日修, 塞下有餘粟, 帑中有羡財, 俟敵果有衰亂之形, 然後一振威武, 恢復舊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 雪祖宗累朝之憤, 陛下功德赫然, 如日照耀無窮矣.
如其不服, 決欲背約, 則令河北諸州深溝高壘, 足以自守, 敵人果來入寇, 所在之兵, 可以伺便驅逐, 大帥持重以全, 取勝自此. 彼來我往, 一勝一負, 兵家之常, 不可前料, 即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 至於清野之法, 則難盡行, 蓋事宜之際, 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糇糧盡入城郭, 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 或有挈家渡河者, 或有留人看守莊舍者, 或有就近入居城郭者, 當使人得自便, 方保安全, 固不可按圖先定, 必令入城郭而居, 雖有嚴令, 必不從也. 在祖宗朝, 屢經北人之擾, 鄉民避寇, 率亦如此, 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
臣歷事三朝, 十年輔相, 官已極品, 歸榮故鄉, 萬事無不足者, 年將七十, 宿疾在身, 每思告老前去, 庶全始終. 比緣聖問之及, 因敢一貢盡言, 非嫉善, 非求進, 用是只以自信. 今天下之人, 漸不敢以直言爲獻, 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 猶覬愚瞽一悟聖心, 爲宗社之盛福, 惟陛下加察, 賜以不疑, 非獨老臣幸甚, 天下幸甚.
弼言, 臣素乏才業, 忝塵二府, 昔在壯時, 精力尙不及人, 今老日病, 氣志衰耗, 何足備大政之問. 然臣實無己見, 今但舉衆人所傳聞者, 錄以上奏, 惟聖明裁擇.
臣五六年來, 竊聞綏州·囉兀城·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 惟交趾中寢, 其餘諸路皆有攻討, 或尅獲, 或喪失, 即傳播天下. 而綏州·囉兀城·熙河始初興舉, 便傳聞云, 朝廷後必復靈夏, 平賀蘭, 既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 此說尤盛. 北人必尋已探知相繼. 彼復聞朝廷修完器甲, 簡練卒伍, 增築城壘, 積聚芻糧, 加之招致高麗爲牽制之援,
近又分置河北三十七將, 按閱愈急, 喧布漸久, 事機參合, 此敵人所以先期造釁, 以有代北侵境之端, 而不肯已也. 其平賀蘭·平燕之策, 虛實固不可知, 然傳者既多且久, 萬口一詞, 誰復辨白. 設有辨者, 遠夷何以取信. 今釁端已成, 代北各屯兵馬境上, 爭議逾年未決, 橫使再至, 事歸朝廷. 此邊臣之職, 而朝廷自當之, 則恐理難欵緩, 便要可否, 違之則兵立起而患速, 順之則河東斥堠窄狹, 爲患雖遲而久遠, 大爲不便也.
臣謂不若一委邊臣, 令其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 使其盡力交相詰難. 然北人非不自知理曲, 蓋故欲生事, 遂興干戈, 以氣吞我, 以勢淩我, 是欲奪我累年所作之事. 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 實有以致其來也, 惟陛下深省熟慮, 不可一向獨謂敵人造釁背盟也. 彼若萬一入寇, 事不得已, 我持嚴兵以待之, 來則禦戰, 去則備守, 此自古中國防邊之要也. 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 臣慮萬一有跌, 其害非細, 更或與西夏爲犄角之勢, 則朝廷宵旰矣. 事既至此, 邊奏警急, 兵糧皆闕, 窘于應用, 須防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 謂國家方事外, 虞其力不能制我, 遂相聚嘯, 蜂蝟而起, 即事將奈何. 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 生民爲念, 納污含垢, 且求安靜, 更俟歲時豐稔, 窮困稍蘇, 流亡漸歸, 民麤安業, 稅賦不失, 倉廩不虛, 恩信宣布, 人心固結, 然後別圖萬全之舉, 貴免一跌之失, 此天下之願也, 亦臣之志也.
向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 中外益更憂懼, 心隕膽落. 陛下雖英睿天縱, 必有成算, 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君, 事體絕異, 尤未可慨然輕舉. 又恐朝廷且作聲勢, 固無實心, 事若如此, 乃是我以虛聲而邀彼實來也. 張虛聲者, 必有疏略之虞. 作實來者, 必有周密之慮. 以疏略之虞而當周密之計, 其成敗豈不灼然耶. 假令入討得志而還, 此契丹一種事方自大, 況又夏國·唃廝囉·高麗·黑水女眞·達靼等諸蕃爲之黨援, 其勢必難殄滅, 使無噍類, 即由此結成邊患, 卒無已時, 大非長轡遠馭之道也.
臣竊謂因橫使之來, 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與云, “朝廷凡所爲武備, 乃中國常事, 非願外興征伐. 向有用武之地, 皆小蕃有過者, 朝廷須合問罪. 若吾二大邦, 通好已是七十餘年, 無故安肯輒欲破壞. 恐是姦人走作, 妄興鬬諜, 或是彼聞我整促邊事, 即疑我有所興作, 我既知之, 豈免大爲準擬, 蓋因此互相疑貳, 養成釁隙, 遂有今日事理.”
朝廷更有可說諸事, 但盡說之, 須令釋然無惑, 乃一助也. 橫使如不納, 即遣報聘者於遼主前具道此意, 庶幾一聽, 必有所益. 緣彼大藉朝廷歲與, 方成國計, 既有顧藉之心, 豈無安靜之欲. 只以欵疑未釋, 遂成倔強. 若與開解明白, 必肯回心向化, 凡百蔕芥, 盡可脫落. 苟互相疑忌, 兩心不通, 禍患日深, 必成後悔.
臣歷觀春秋洎戰國時, 諸侯遞相征伐, 兩兵已合, 飛矢在上, 走使在下, 其間辨說解釋, 遂各交綏而退, 卻復盟好者, 比比皆是. 況今釁端漸啟, 兵尙未合, 且可多方以理解釋, 或能有濟, 與其用戰征而決勝負, 萬不侔也. 此致疑及禦戎二事, 臣並得之羣論, 非出胷臆, 是皆目前衆所共知共見必然之理, 必難事外別求奇異之策也. 臣皆望陛下兼求博訪, 不宜專聽一偏之說, 恐有逆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 不敢盡以實事上奏, 有誤國家大計.
臣今所以及此者, 竊聞去春以久旱, 陛下特降手詔, 許人極陳朝政得失, 中外歡忭, 咸謂聖情已大開悟, 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 隨而或遭貶降, 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優容之, 反令得罪, 士大夫自此皆務鈐結, 忠藎之言不敢復出於口. 臣謂下情不能上達者, 乃朝政莫大之患也, 願陛下深思之, 極慮之, 早令天下受賜及朝廷無事, 不勝大幸. 此奏出于怱遽, 又且欲事理明白, 不敢少加文飾及援據古事, 但直書利害而已. 昔楚相子反謂區區之宋, 尙有不欺人之臣, 況中原大國, 已與北人結隙, 今若更不推誠以待之, 則恐不能解疑釋惑也. 伏乞聖造特加裁恕.
彥博言, “敵人之情, 貪利忘義, 然自祖宗朝與之通好, 息民幾八十年, 未嘗犯順. 惟慶曆初乘我西事未弭, 故有邀求, 當時再立誓書, 亦古尋盟之義. 自數年前, 累來妄理白溝館地及要拆去鋪屋. 況誓書之中, 明載雄州所管白溝, 兩朝遵守已久, 且信誓之辭, 質於天地神祗, 告於宗廟社稷, 此而可渝, 何以享國. 今蕭禧重來, 又決於雄州北亭交割禮物, 其意欲以雄州北亭爲界. 原其貪心, 亦因慶曆初西事未平之際, 來求黃嵬之地, 朝廷容易棄與之耳. 然中國禦戎守信爲上, 必以誓書爲證, 彼雖詭辭, 難奪正論. 臣又以事理度之, 事固有逆順, 理固有曲直, 若敵人不計曲直利害, 敢萌犯順之心, 朝廷固已嚴於預備之要, 足食足兵, 堅完城堡, 保全人民, 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 止此而已. 大抵中國之兵, 利在爲主, 以主待客, 以逸守勞, 理必勝矣. 竊料聖意重於舉動, 發言盈庭, 容有異論, 或曰先發制人, 意在輕動. 或曰乘其未備, 襲取燕薊. 事不審處, 恐將噬臍, 非王師萬全之舉也, 伏願陛下垂意熟察之. 今朝廷分置將官, 整齊器械, 固得之矣, 然將校偏裨, 更須遴擇其人. 又河朔薦饑, 若兵連未解, 物力殫屈, 即金湯不守, 先事而辦, 乃無後艱.”
公亮言, “國家以通和之策羈縻強敵, 雖歲委金帛, 而休兵息民逾七十年. 近者數起釁端, 蓋欲自庇, 不然, 亦謀之舛謬. 代北之地, 詳詔旨所諭, 以爲官吏按行圖籍甚明, 則雖欲包含, 亦恐無名, 與之無名, 則無厭之欲後不可足, 且敵人之情, 畏強侮弱, 要在控制得術耳. 嘉祐以前, 西夏頗守誓約. 嘉祐元年, 妄爭麟府封疆, 遂擄·郭恩·武戡·黃道元·朝廷姑務含容, 無一言問罪. 至治平二年, 又妄認同家堡以爲封境, 殺掠屬戶弓箭手數千·牛馬萬數而去. 已而檢視同家堡地界, 乃元昊時生蕃十九戶所獻, 遂降詔諭之. 諸司副使王無忌齎詔至境, 拒而不納, 朝廷不欲深治, 但命延州牒問, 遂攻圍大順城, 諒祚中流矢乃去. 其後雖遣使奉貢, 而屢入寇邊, 乃詔權罷歲予, 方復懇求, 待之如初, 因而帖服者八九年. 臣思北敵之情, 恐不異此.
臣之愚慮, 欲乞朝廷選擇謀臣報聘, 諭與彼國生事, 中國包含之意, 至於疆界, 案驗既明, 不可侵越, 使敵主曉然, 不爲邀功之臣所惑, 必未敢萌犯邊之意. 且中國今日之勢, 與雍熙·景德之間不同, 河北之兵, 既以倍增, 又益之以民兵, 及行陣訓練多出睿算, 以此待敵, 不爲無備. 然尙須謀擇將帥, 北邊久不用兵, 雖有可用之人, 或未之試也. 若將帥得人, 委之一面, 使久其任, 觀其措置才略, 足試後日之用. 或謂河北久戍之卒, 不經征討, 則陝西·河北近有戰勝之兵, 自可籍記, 以備一旦調發. 敵人萬一犯邊, 願先絕其歲賜, 臨之以良將精兵, 彼亦自亡之時也. 景德中, 敵騎南牧, 一遇親征之師, 狼狽請盟, 若非眞宗憐其投誠, 許爲罷兵, 無遺類矣. 況今日備禦之勢, 又非昔時之比, 但定州一路最爲控扼, 若入寇之初, 勿犯其鋒銳, 俟其入界疲曳, 以重兵夾攻, 必無不克. 敵若敢深入內地, 則臣謂大河之險, 可敵堅城數重·勁兵數十萬, 寇至北岸, 前臨大河之阻, 後有重兵扼之, 前不得進, 後不得奔, 王師仍列強弩於南岸待之, 此百勝之勢也. 今者中國所以待敵人者, 既極包容矣, 若其生事不已, 不使知懼, 臣恐未易馴服. 控制之柄, 無使倒持, 北敵知中國之不可窺, 姦謀亦自息矣.”
색인어
- 이름
- 蕭禧, 呂惠卿, 蕭素, 梁穎, 劉忱, 呂大忠, 韓縝, 王師約, 李憲, 沈括, 張奉遠, 白友, 聶再友, 曹彬, 米信, 彥博, 蕭禧, 公亮, 郭恩, 武戡, 黃道元, 元昊, 王無忌, 諒祚, 眞宗
- 지명
- 橫都, 西陘, 長連城, 六蕃嶺, 長連城, 六蕃嶺, 契丹, 長連城, 六蕃嶺, 關口, 把鋪, 代州, 崞縣, 赤埿膠, 長連城, 契丹, 李福蠻, 水峪, 西陘寨, 黃嵬山, 瓦窰塢, 代北, 石晉, 高麗, 契丹, 浙路, 秦州, 吐蕃, 熙河, 河州, 河朔, 河朔, 北京, 澶州, 雄州, 北朝, 代北, 雄州, 河朔, 岐溝, 河北, 綏州, 囉兀城, 熙河, 交趾, 綏州, 囉兀城, 熙河, 賀蘭, 河北, 代北, 代北, 河東, 夏國, 唃廝囉, 高麗, 黑水女眞, 達靼, 黃嵬, 河朔, 同家堡, 延州, 大順城, 河北, 陝西, 河北, 定州
- 서명
- 春秋